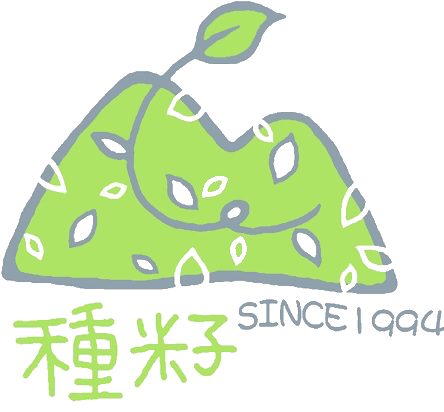【瑋寧說說話--選擇】
20140106 瑋寧
理念的最佳表達方是不是我們的話語字句,而是我們作出的選擇。
期末到了,學校有好多事情分線在跑。
校外教學回來緊接著是文化日,文化日後接著學校評鑑。
有疼愛老師的家長在行政室聊天時說:「終於可以告一段落了吧?! 」
我們笑著回答:「告哪一段落啊?」
種籽的生活很像無間道,除了課程收尾、畢製畢挑鋪陳、期末晚會、期末評量、期末對談,還有下學期的課程安排現在就要開始了啊!和這些生活事務平行在跑的呢,還有伴著教師進行生涯發展的教師成長機制、寒假的教師工作與進修,以及醞釀進行中的種籽課程統整—我們一直在想,除了九年一貫的分類方法之外,我們還能怎麼論述孩子在學校經歷的課程經驗?
種籽教師團要面對、處理的事情,跟一般經驗中的老師不同,從一所學校的結構到零件,從孩子成長的骨架到靈魂,從辦學的時間到空間,三不五時,土石還來挑戰老師們的神經系統。
清鏘清鏘清鏘鏘,難免,到了學期末,會覺得自己像是一列向前衝的火車,一邊衝,一邊記得靠站,一邊,有些零件還沿路往後掉……
這種時候,腦袋裡總是噹噹噹響起一句宜珮常常掛在嘴邊的話:也沒有人逼我們啊,誰叫我們選擇辦學校?!
是,深呼吸,誰叫我們選擇辦學校?!
打開電腦,google「選擇」兩個字,想看看跳出來甚麼,首先是林子祥與葉蒨文的歌,然後是選擇權、選擇性失意、選擇困難症……
然後讀到比較有感覺得一句話:選擇是一種有智慧的放棄。
再來,據說是美國曾經的第一夫人Eleanor Roosevelt說的:理念的最佳表達方是不是我們的話語字句,而是我們作出的選擇。
最後這句,敲了一下我的心。
我們總是說,在種籽,我們練習選擇與承擔。
首先第一眼,最容易發現的練習就在語文與數學必修的選課制度裡。
種籽的選課制度設計,其實搭配的是站在互信基礎上的親師合作,以及導師制度。選課時,我們可以理解孩子的第一反應,他選甚麼?不選甚麼?選了,是基於甚麼原因?不選,又是因為清楚自己當下的道路?還是因為迴避?
老師們開學時會以對孩子的了解為基礎,依照不同的年齡發展,大約從中年級開始,和孩子們談談孩子作此選擇當下的狀態,或是作此選擇的意義,或試著和孩子談談他的特質和學習任務,年紀更大一點,還可談談當你「不選」的時候,其實你是選擇了什麼?老師們會把孩子的課表每學期留檔,需要的時候回頭看看孩子的軌跡。至於低年級,在選擇的練習與執行中,孩子們有機會卻時感覺他的權利,因此有朝一日,他比較有可能清晰的感受到相對應的責任與承擔。
無論我們跟怎樣個性、怎樣發展階段的孩子工作,我們都會記得一個底—選有的選擇都是一種經歷、一種練習、一種可能性。
把鏡頭再拉遠一點,種籽的選擇真是無所不在。
因為種籽的活動空間有限,我們選擇藍球場保持多功能,所以便要承擔腳踏車、舌板、直排輪刮傷球場鋪面。
因為選擇邀請昆蟲和候鳥來到校園,所以我們維持不開發杉木林和大草原,選擇不用除草劑處理球場上的青苔。
因為選擇辦學自主和人事自主,我們才能掌握學校的氛圍和不致搖擺的核心,所以我們在法令下選擇沒有政府補助的辦學成本。
種籽總是想創造一種氣魄:沒有完美的選項,只有作選擇並為之負責的勇氣。
一如王浩威在作品中提過的概念:每一種教育作為都可能解決部份問題,也必然會遺漏一些問題。我們作出的所有選擇,都會有一種後果,在其中,你得到一些,你失去一些。
有些人說:太多選擇讓人不快樂。也許真正的底是—太多選擇,人沒比較不容易看到自己選擇的,而容易看到自己沒有選的,然後,就基於習慣不缺的生命經驗而害怕出手了
如果同意這個邏輯,下一個問題便是:我們究竟依據甚麼在作選擇?
是擔心選擇不正確?結果不圓滿?缺了?漏了?少了?不足了?
還是我們可以偷到生命中的一點點泰然,去迎接我們選擇的,然後把合理的不選擇也看作是一種值得存在的選項?
今年,有一群據說叫做白腹鶇和赤腹鶇的候鳥選擇在種籽暫時落腳;持續的寒天裡,櫻花陸續開放;大人小人們在校園悠閒的悠閒、忙碌的忙碌,我就這麼把你們都當老朋友碎碎唸著。如果拗口,請原諒我這前奔跑、往後掉零件的火車。
後面附上一篇文字,Once Upon A Time,一篇曾經的書寫,大概也有三分之一的種籽家庭沒有讀過。文裡提到的創造,以及變與不變,也都是選擇啊!
瑋寧說說話 Once Upon A Time…… 20100523
這學期,一走進種籽,很容易就會看到行政室門口貼的「法官當選名單」,法官當選人名字正正式式的用書法寫在紅紙上,這些當選人,可是經過提名、投票和唱票程序,由全校大人小孩一票一票選出來的。
這是種籽今年的新嘗試,目的是讓大家好好思考法庭的意義,以及法官的任務和榮譽。以往種籽也會在每學期初選法官,不同的是,以前大家會在生活討論會上題名然後直接投票,然而這幾個學期,老師們感覺,好像慢慢有點像是選人氣而不是選法官了,於是提出這個新辦法,想試試看情況會不會有所改變。
這學期來學校參訪的客人見了,總是以為這樣的票選程序和這張紅紙名單,是學校的傳統。這時,我總是笑笑的說:沒有耶,我們也是第一次做這樣的嘗試,而且,還在研究這樣的方法是不是要繼續下去。
我覺得,這是在種籽常見的誤會。大家很容易感覺這裡運行的大小事務,都已經行之有年,是個確定的慣例或制度。
以校規來說吧,如果你看到蛇板規則在孩子心中如此明確,就以為蛇板規則在種籽行之有年,那就是個誤會啦!蛇板在種籽出現,不過一年左右的事,所以蛇板規則在種籽差不多也是這樣的歷史。
如果你以為,交通車本來就是固定位,那也是個誤會,原本每天自由選位的交通車大概是這兩三年,才在各種因素的考慮之下,變成固定位的。
不講校規,講生活吧。你看一大群孩子在廣場上玩「建國遊戲」玩得眼神如鷹,進出自如,感覺「建國」和「佔條仔」一樣,都是種籽歷史悠久的遊戲,那更是個誤會,李航教孩子們玩「建國」,距離現在不會超過兩年的時間。
再細緻一點,親師懇談出現低年級特別場,是這兩年的事;運作的嚇嚇叫的週二三四餐廳,從去年開始;小樹屋的沙袋,今年才出現;鄉運出現卡轟和海盜旗,是令人驚喜的第一次;前後十二年種籽去了三次蘭嶼的確是事實,但是種籽老師浩浩蕩蕩帶著九十多個孩子去蘭嶼,卻是第一次。
為什麼有這麼多變動呢? 這些變動的背後,有什麼意義?
有。許多變動背後共同的意義,其實是為了維持核心與信念的不變。
隨著時間與歲月流轉,種籽面對的大環境不一樣、家長不一樣、孩子不一樣、連教師團的組合也不一樣,這些實實在在與種籽運作相關的不一樣,都需要關照思考。許多事情,在想法作法上,都得要有願意改變的心理準備和能夠改變的彈性,才能夠張開最大的關照網。而大家之所以有能量禁得起這些改變,以及改變帶來的後續,則是因為相信種籽精神裡不變的價值。
我又要比如說了。
因為在意種籽法庭的價值,所以翻攪了原先的選舉程序;因為在意與孩子一同「長」出學校的規則,所以蛇板規則得在生活討論會上討論通過;因為在意親師合作,所以調整溝通方式;因為在意與孩子一同創造成長中的生命經驗,所以克服各種限制與改變繼續五天四夜大旅行……
我的意思是,種籽有許多「想當年」的故事,如今在其中生活的我們,除了聽著「想當年」,還得記得專注於當下的創造。而這些想當年,都是現在最好的養分與參照。
小劇場的楓香很堅定的告訴我們:夏天到了。接下來,先是種籽日,然後就是畢製收尾、畢業晚會與畢業挑戰,接著,又是新生試讀,又將有一批新的大人孩子成為種籽的一份子。如果沒有人去說故事,他們大概會認為小樹屋的沙袋一直在那裡,而卡轟,是種籽的音樂傳統。
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……故事通常都以這個句子為開頭。至於王子和公主是否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? 我不知道。因為他們的日子還在過下去,怎樣在變與不變中找到幸福秘方?我想,應該可以是每個王子和每個公主茶餘飯後的好話題。